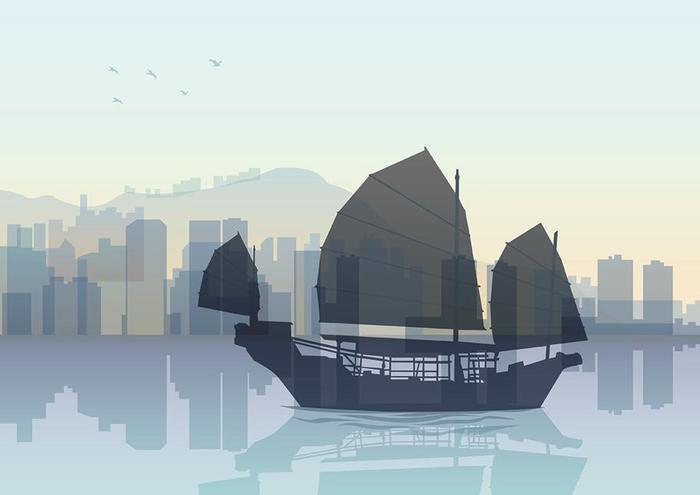新福事工協會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為回應社會上貧窮人士的需要,提供很多不同的服務,包括:匯聚社會資源的社區及資源中心、宿舍服務等,受益者眾。本社同事走訪了不同的服務使用者,希望協助大家「看見」社會上一群有需要人士的境況。
讓兒子健康溫飽最要緊
受助人:阿菊(化名)
阿菊原本居住的地方,租金便宜,但衛生環境非常惡劣,天花的石屎剝落,但業主不肯付錢維修,她既擔心安全,又擔心兒子的濕疹會惡化,從朋友處得知新福事工協會(新福)有一個津貼租金計劃,她就向新福同工講述自己的情況。同工認為她的情況符合計劃的條件,於是決定幫助這家庭改善居住環境,協助他們搬入現時100多呎的居所。地方雖然細小,但五臟俱全:獨立廁所,開放式廚房,「碌架床」,風扇、冷氣機、電視、雪櫃、洗衣機等一應俱全。兩母子總算有一個安全居所。由牆上的掛畫,可見她的兒子的畫畫天份不錯。
阿菊的丈夫失蹤多年,突然以分居超過兩年為由單方面向法院申請離婚,離婚後,前夫不願給贍養費。現時九歲的兒子,因為早產以致智力不健全,需要入讀特殊學校,加上患上睡眠窒息症,每小時平均會停止呼吸四次,她擔心兒子會一睡不起,於是,每隔15分鐘便要拍醒他。這樣的情況,弄得她不能安睡,精神狀況非常差,只有等兒子上學後,她才可以安心睡覺。另外,因為兒子的濕疹,阿菊擔心他的健康,每天都會將家居打理得一塵不染。因為要照顧兒子及打掃房間,她根本無法外出工作,每月只靠兒子的綜援金及傷殘津貼約7,000元生活。由於租金已佔了大半津貼的開支,她只好在食物上節省金錢,有時會去食物銀行取一些乾糧及米,有時陪兒子吃完早餐,為了節省金錢,自己連午餐也不吃,將節省下來的錢買些肉給兒子。
另外,每年暑假她們都會回鄉,一來可以減低生活開支,二來阿菊父母可以協助照顧兒子,她可以到朋友處做一些工作,賺取一些生活費。她回鄉居住時亦會刻意預備炸魚給兒子吃,希望兒子可以有多些營養,能夠身體健康。
訪問當晚問阿菊會煮甚麼晚餐,她就從雪櫃取出一包菜、一碟吃剩的食物及一包麵……就是這樣簡簡單單的一餐,最緊要,吃得飽!
亞杜蘭宿舍──讓軟弱的聚集到這裡來
無言感激 尋找新盼望
受助者:阿傑
阿傑,年約30歲,從事銷售業,於2013年年底認識了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的社工何先生(即阿傑口中的阿圻)。
當年他正面對失業,又已到最後限期仍沒有錢交租,差不多要流落街頭,帶著極度徬徨、無助而且失落的心向朋友求助。短短一週時間,阿傑便獲協會安排面談接受評估、驗身,然後搬到臨時宿舍居住。在宿舍住了兩年,經同鄉介紹,決定嘗試搬到旺角一個約3呎乘6呎的「床位」居住。那邊的居住環境十分侷促,不單沒有任何公共空間,更要八人共用一個洗手間,連想「透氣」的空間都沒有,卻已經要繳付2,500多元租金。對於月賺約萬元的阿傑來說,實在不算得輕省。碰巧阿傑那段時間又經歷工作環境的轉變,加上居住環境惡劣,而與該房子內的「鄉里」關係冷漠,偶然談起鄉下的情況卻令阿傑更加思鄉,因而情緒十分低落。
一次機緣巧合下,協會一位有心人聽到阿傑的住屋分享,二話不說決定要借出一個單位辦新宿舍,亞杜蘭宿舍得以成立。搬離半年後,阿傑厚顏地向阿圻表示希望可以搬進新的宿舍。
曾經住進宿舍,亦試過搬離,最後選擇回到宿舍,對於阿傑來說,最大的轉變是讓自己可以計劃將來。之前因環境的壓迫令他對未來沒有甚麼盼望,但在宿舍最少讓他有空間反思,而且與宿友之間那份情誼和支援,讓他有放鬆與喘息的空間。阿傑甚至以戰友形容同住的宿友,當中那份淡淡的、男人之間的支援教他感動。
提到雖然大家的年齡有差距,並不是無所不談,但大家的背景相近,都會嘗試直接表達、以禮相待、彼此遷就,當中可能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而有不咬弦的時候,但都盡量不禍及他人。而宿舍每月都會有「例會」,讓當中的舍友都能坦誠溝通。宿舍的生活相對安穩,但阿傑對未來仍有計劃,希望將來能轉換新的工作、找到套房租住。阿傑坦言,對於未來,自己都有憂慮,特別面對嚴重的居住問題,即使想搬離都不一定有足夠能力,如搬離後又再重新經歷一次「旺角」床位的經驗,對阿傑會是另一次難以想像的恐懼與折磨。
「宿舍是讓這群人(無家者)看見希望的地方,在緊張的生活讓自己有放鬆的空間。真的好多謝他們,希望協會可以幫到更多我們這類人。」阿傑靦腆地說。透過阿傑的分享,聆聽他對宿舍建立的歸屬感、對宿友關係的珍惜、對同工的感激,深深感受到住屋對他的影響;亦感到他對阿圻和協會那份無言的感激。
暮年飄泊 何處是吾家
受助者:阿斌
年過60歲的阿斌,2015年年底因家庭的問題而流浪街頭,只能睡在通宵營業的快餐店,他以「簡直想死」去形容當時的心情,最後決定走到社署尋找支援,社署把他轉介給協會。協會安排他兩天後搬進臨時宿舍,住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在2016年年底搬到亞杜蘭宿舍。
阿圻除了協助阿斌解決住宿的問題,亦會就他的問題給予建議或其他幫助。從睡在街頭到搬進宿舍,阿斌坦言從很低落的情緒走出來,亦很感激阿圻對他的協助,讓他在迷惘中找到一些方向。對於一向獨立的阿斌來說,要適應不同的居住環境並不困難,豐富的人生閱歷亦讓他較容易與不同的人相處。現在的情況一切看似很不錯,當提及未來的計劃,阿斌的眼中不期然滲出淡淡的哀愁。由於宿舍的住宿期為兩年,對於曾經享用公共房屋服務而不能再申請的阿斌來說,一年多後需要再回到自由市場尋找居所,會有更多的挑戰。
阿斌的情況,正正代表著一群正在步入暮年,身體仍然健壯,卻又面臨即將退休,而又無法輪候公共房屋或安老院舍,但社會福利又不足以支援的一撮人。在可見的將來,這群人似乎看不到出路,到底整個系統可以如何照顧到他們的需要呢?
誠然,要推動政府改善安老或房屋的政策,的確不容易。即便如此,仍盼望社會不同的持分者能向政府施加壓力,令她正視人口不斷老化而需要做出相對的政策制訂。與此同時,教會作為地上的燈塔,當擁有一定的資源、聯繫和能力,能否領受這個異像,服侍這群有需要的人?假如教會已預定部份的資源去賙濟窮人,祝福社區,除了物資或食物銀行等方式,又會否考慮以多元性的方法去關懷貧窮人呢?
在關顧貧窮人的層面中,教會可以把眼光放得更寬更廣,在資源上照顧他們的同時,更讓他們在生命中找到盼望,相信是對他們最好的祝福。
越過生命低谷 成為社區祝福
聆聽兩位男士分享過後,有機會與阿圻傾談。阿圻表示男宿舍與女宿舍最大的分別是協助他們建立支援網絡的情況。男性與女性的性格很不一樣,女性很容易就可以建立關係,但男性很多時都自行解決問題,各自為政;然而宿舍成立的目的,除了讓他們可有暫時的安身之處,亦盼望能讓他們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群體,彼此支援守望,亦希望打開他們的眼光,讓他們看到自己身上的優點和資源,以致他們離開宿舍後,仍能夠善用已建立的資源繼續生活,甚至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被愛感動信主亦決意要助人
受助人:阿婷(化名)
去年7月帶著女兒來港一心投靠丈夫,怎料他把她們趕出了街頭。她們沒地方住,就在體育館旁邊的地方住了數天,幸好遇上有心人帶她們去見區議員,再經社工轉介,輾轉來到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在「恩福之家」住了兩個多月。
阿婷女兒的眼睛及手指有毛病,要分開兩段長的時間做手術,需要有好的環境休息,就被調遷到協會另一所更適合她們,可以較長期居住的「以斯帖之家」。
據一同接受訪問的協會高級宿舍主住施小姐指出,「以斯帖之家」是由一位有心的弟兄以平價租給協會作中長期的宿舍,令人可以安居,並思考之後要走的路。
因為阿婷為新來港人士,她的情況除了需要人關心之外,還需要學習廣東話,並認識香港這個地方。協會藉著讓她很輕鬆的參與Alpha Course信仰小組,學習接觸信仰,亦鼓勵她放膽以廣東話分享,亦關心她、為她禱告。「最感動的一次,是首次有義工為我祈禱,淚就流下來了。心就被打開,很舒服……以前很無助,很煩惱;但現在我覺得很開心,這裡給我感覺得溫暖,似是一家人。」
最後,阿婷亦分享到,經歷了被人無私的幫助後,她決定要做好自己,有機會亦會幫助別人!她還鼓勵女兒,得到大哥哥們悉心教導功課後,長大了還要幫助其他的小朋友呢。
放下壓力心境變得平靜
受助人:阿雲(化名)
阿雲在港住了多年,與丈夫育有一名兩歲多的兒子。但近年丈夫的脾氣變得很差,要她千依百順,否則會亂擲東西和罵人,嚇怕了小孩。很多時更會在半夜或未天光時吵吵鬧鬧,令阿雲兩母子失去了安全感,只可以與兒子抱著哭,亦感到沒人可以幫助。直至有一天,她丈夫把她們趕了出去。
兩母子先入住向晴軒,及後再轉到屯門的百合之家。「百合之家為屯門區一所中轉家舍,是一位有心的弟兄聽了協會的分享,受感動而買了樓高兩層的房子改建成為家舍,給屯門一所教會(青山浸信會)去管理,以服侍有需要的人。協會的角色是支援、提供管理建議及運作經驗,並分享理念及傳遞價值觀。」協會的施小姐補充道。
阿雲覺得在家舍感受到被愛及關心,也放下了可能會居無定所的憂慮。而且其他的舍友都很友善,亦互相關顧,會照顧她的兒子,兒子在被愛的環境下,脾氣都改善了很多。而阿雲亦積極參與協會舉辦的課程,如:化妝班及遊戲治療,讓自己可以學習建立自信心,放鬆、放膽去表達自己,更可以了解自己和定下目標去改善自己。
阿雲認為以往的自己是很封閉的,很少與其他人相處、傾談。反而現在,因為接觸的人多了,人也開朗起來。而且,也開始做義工,幫助在家舍中認識的新手媽媽,煮飯、給她們送飯、替她們洗衣服……「自己都曾經歷過新手媽媽的辛苦階段,能夠幫就幫吧。」
協會的施小組最後亦提到,希望更多人可以參與,提供資源或開始去關心香港貧窮人的居住問題:「因為這是香港現時一個很嚴重、亦很切身的問題,需要大家關注。」她盼望有更多的教會可以開始與弟兄姊妹去關注,並伸出援手。
協會更為女性住宿者成立一個「娘家會」,讓她們可以回來,建立友誼、互相扶持之餘,亦可以站出來再去幫助別人,使這「娘家」可以再有繼續發展的空間。
後記:
每人都會經歷到有困難、需要被幫助的時候。訪問及記下受助者的經歷,讓我們知道伸出援手不但可解燃眉之急,亦可讓他們重得人生方向。社會上仍然有許多單身人士及家庭正面對嚴峻的居住問題,協會不單止走到前線去協助有需要人士,他們亦會分享經驗以鼓勵及協助教會和主內弟兄姊妹去設立家舍,並成為義工,協助青山浸信會設立屯門百合之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盼望神能興起更多教會和弟兄姊妹勇敢地踏出一步,走進這愛心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