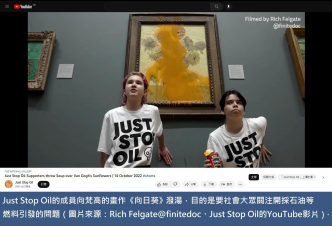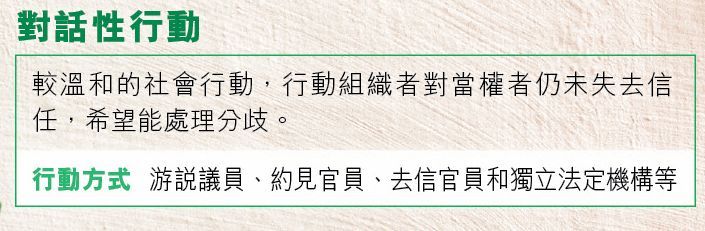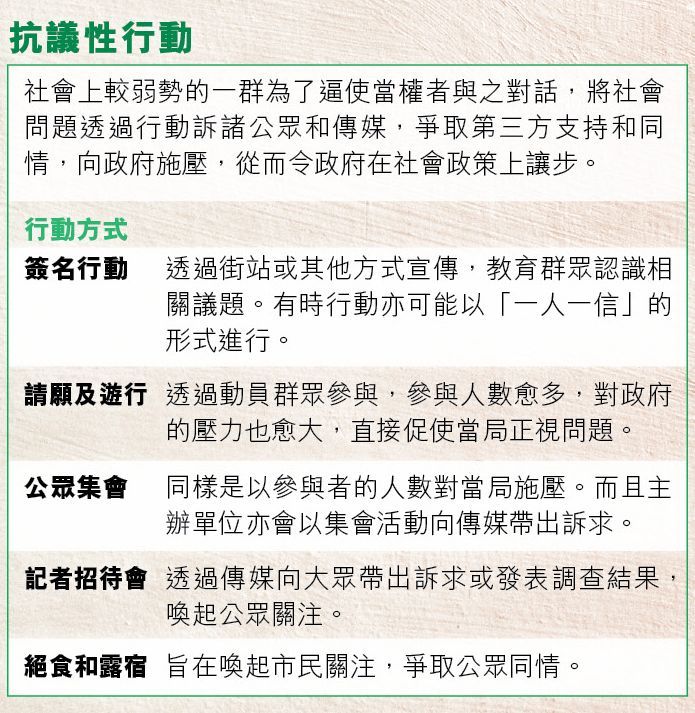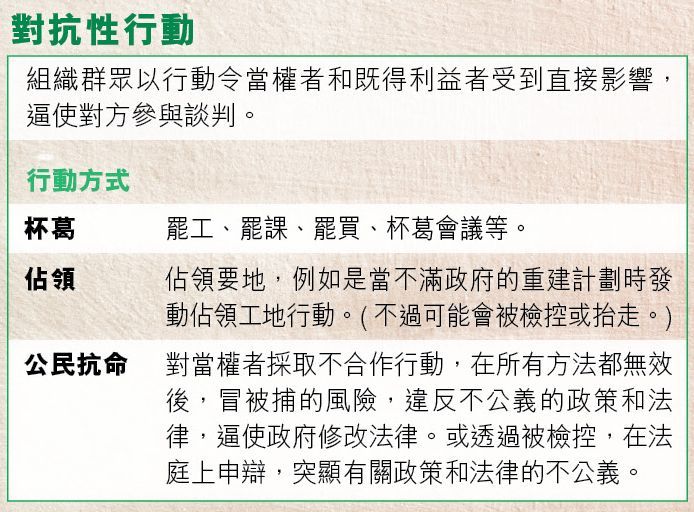自從2019年,社會對用激進手段進行的抗爭,看法兩極。贊成的一方,認為抗爭者本來想用傳統寫信、簽名等方式表達意見,但完全沒有反應,所以才用較激烈的抗爭,而且只有激烈抗爭,社會才會感受到切膚之痛和需要,這樣才會帶來改變。但反對的一方認為,社會抗爭太激烈,影響民生的話,既不能得到社會支持,甚至倒過來會招人反感。
近月最出名的例子,莫過於環保團體Just Stop Oil的抗爭活動,整個暑假在英國不同的高速公路堵路,在政府機關建築物的外牆噴上漆油,甚至到博物館將罐頭湯潑在名畫上。當地警察單在今年10月就動員過萬警員去處理這團體的大大小小行動。由9月底的至整個10月,當地警方共作出677次拘捕行動,111人被告。
與真正的暴力抗爭不同,Just Stop Oil的做法並不真正破壞任何物件,例如他們倒罐頭湯的行動中,他們宣稱只會倒湯在有保護的名畫上,所以最後該畫不會受到任何影響,之後再加一句:「難道你重視名畫的安全,多過地球嗎?」[1]
環保團體做類似的行動,動機明顯,亦看出整個計劃在行動前有思前想後,他們說堵路只是為了給予大家機會去思考甚麼才是當前最重的議題云云。看上去理性,透過行動希望喚醒更多人回應,但實際上並不如此。曾經做過環保團體的發言人,但不喜歡這種抗爭手法的哲學系教授Rupert Read坦言,這種做法雖然能引起社會關注,但最後真的能成功動員的人口,可能只有百分之二。[2]
他認為透過這類激動抗爭,並不能帶來廣泛共識,只會令社會走向兩極,而且會持續失去支持者。實際上Just Stop Oil 的發言人也表示收到不少人的投訴信,要求他們就這些抗爭行為帶來的影響道歉,但他說機構不會這樣做,他說:「巿民絕對有權對我們的行為表達憤怒,但問題是為甚麼會憤怒?我們今日已經沒有時間再談如何提升大家的意識,我們需要行動。」[3]
公民社會或者壓力團體可能只從政策能否被有效倡議的角度去討論問題,但如果從政策制定的角度出發,很多人自然會問:堵路犯法嗎?淋湯到名畫上犯法嗎?答案是肯定的。在香港可能大家今日會想到用國安法處理相關問題,但在英國,他們本身就有法例處理公路的破壞行動,也有法例處理破壞名畫的行為。這些行為違法,參與抗爭的人也知道,也有準備會上法庭。當然,他們一樣會用盡法庭給予他們的人權和自由去爭取和抗辯,所以一樣會籌錢打官司。
同時,社會亦質疑現時的法例會否令警察難以執法?英國本身強調人權自由,集會、示威、言論自由均受到社會重視和保障,但激進示威者透過破壞社會秩序,企圖喚起巿民關注他們所關注的議題,這方法合法嗎?根據BBC的報道,理論上堵路、破壞物件本身就犯法,某些行為例如拉人鏈入馬路,就未有法例明確禁止,即使警察有法可依,但該法例未有針對示威者這類行為,也沒有特別的指引,因此警察執法確有難度。[4]
為此,英國政府正審議公共秩序草案(Public Order Bill),規管有關的行為,例如堵路、人鏈、干擾公共設施的使用等,又加強警察截停搜查的權力,有關法例當然被一些支持透過遊行示威表達意見的機構所反對,[5] 認為這些做法侵犯巿民的基本人權和表達意見的自由,要求取消有關的立法,但當社會日常運作受到影響,高速公路,甚至電力可以被干擾時,有沒有法例可以快速令社會回復正常,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討論點。
從社會抗爭的角度來說,激進抗爭這種做法和武俠小說裡的七傷拳一樣,雖然可以達到行動者想要的效果,但同時會令自己受傷。健康的公民社會本來就應該聆聽巿民和壓力團體的想法,透過社會一起參與討論協商,謀求解決的方法,而不是透過破壞來企圖令對方就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當中部份方法的確有爭議,這些方法應該要在必要情況下,並獲得社會較大共識才可以使用。同時,英國政府理應反思,透過增加警權去「管制」社會抗爭者,實際上未有解決他們本來所提出的議題,正如Rupert Read所言,這些做法只會令社會更加兩極化,而不會有機會成功回到會議桌,尋求解決的方法。
[2]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2/oct/30/are-disruptive-tactics-winning-hearts-minds-bid-highlight-global-heating
[3]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2/oct/29/just-stop-oil-protests-roadblocks-activists-direct-action-climate